作者:InsSeo 发布时间:2024-11-27 11:40 分类:谷歌词库 浏览:383
一
我发现妈妈这个人,总是同别人想得不一样。同时,她好像 不是生存 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事事别出心裁 ,然而又到处 碰鼻 。不外 她从来不因此懊丧。她气愤 的时间 ,就倒在床上看书,从枕头下拽出一本《格林童话》或是《伊索寓言》什么的,看着看着,她会“扑哧”一声笑起来。我问妈妈你笑什么呀?她还笑个不绝 ,她说来来来,过来,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她就讲《幸福的汉斯》、讲《狐狸和猫》给我听。讲完以后要是问她,妈妈你刚才为什么气愤 ,她笑哈哈 眨着眼睛说,哎呀刚才我是气愤 了吗?你看,连我都忘了那是为什么……
母亲的政治受难史
悲剧
当时 妈妈学校的墙上,已经出现了很多 大字报。我知道那叫“大鸣大放”。我每天 都在那些大字报底下钻来钻去,和小朋侪 捉迷藏。但是妈妈很少在那些大字报下停顿 。她走过墙根时,步子总是急遽 忙忙又丢魂失魄 的。
天空乌云密布,一场更大的狂风 雨,席卷着棍棒刃剑倾注 而下。一九五六年的“肃反”活动 刚刚已往 不久,反右活动 又开始了。
那些日子妈妈的右眼总是跳个不绝 ,她以为 一场劫难 又要到临 了。就学校的这些老师来说,她大概可以算是唯逐一 个“三位一体”的“人选”了。--她出身 于剥削 阶层 家庭、父亲是个被判过刑的“伪镇长”;她的丈夫是个劳改刚返来 不久的“汗青 反革命”;而她本身 ,汗青 上曾经被捕,一九五六年再次确定的审干结论上,还是 以为 她有“自首举动 ”,没把她打成“叛徒”,已是万幸的了。就她如许 的政治状态 ,只要说错一个字、一句话,都将跌落万丈深渊,万劫不复。她是一只地隧道 道的瓦锅,且已是遍体裂纹、遍体鳞伤 。不要说有只铜锅来撞她,就是漂来另一只瓦锅,不经意地一碰,霎时 间土崩瓦解的,只能是她。
那段时间,妈妈整日里沉默 沉静 寡言,连故事也不给我讲了。
就在“大鸣大放”最热闹那会儿,有一天妈妈低头颠末 大字报前,她知道大字报的内容,大多都是反映有关知识分子报酬 的,比如 西席 的宿舍太拥挤、讲授 条件太大略 、学校党支部有官僚主义作风等等。妈妈固然 内心 同意 这些意见,但她却不肯 也不敢出头露面。因此当有一天,同一个教研室的老师拦住她请她署名 时,她有些迟疑不决。她明知道本身 不应 署名 ,但不签又以为 对不住同事。她把本身 的名字写得潦草至极,潦草得险些 看不出是谁。
……
开始有人检举检举 朱小玲的反党言论了。
所谓的“反党”言论,是说她曾经穿过一件银灰色的海孚绒大衣,上班时对×××说,你看这大衣还是 我完婚 时,父亲送给我的,当时 也不贵,如今 怕是再也买不起了。
明摆着,她这不是在散布“今不如昔”,又是什么呢?
又说她认识 一个叫刘季野的人,那人是杭一中的语文西席 ,一九五五年被打成“胡风分子”。她同他有过来往,应当诚实 交代 她和他之间的反动言论。
尚有 人说她想让女儿学弹钢琴。带女儿去看戏,从来不看当代 戏,看的都是什么外国歌剧或是莎士比亚的话剧;给女儿买的书,险些 没有几本是中国书,她这不是作育 女儿走白专蹊径 ,又是什么?从这些究竟 可以看出,她的资产阶层 头脑 多么 严峻 ……
同一个学校的老师中,那些出身 好的、那些丈夫是武士 或是干部的、那些刚从师范毕业 的、那些汗青 明净 的……都像是压在妈妈头上的砖块,一层层越垒越高、越砌越悬,一块块压得她喘不外 气来。可她却有口难辩,连表明 的大概 都没有,唯恐言多有失。
“瓦锅”内心 明白 ,她必须在本身 那易碎的外壳上,想法 裹上一层防护的布、油毡、三合板或是别的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她不能就此任人摆布、由人宰割。她只有本身 来救本身 。而且应在校领导 作出末了 的决定之前,反守为攻、转移目标 ,先把本身 从火力的中心 摆脱 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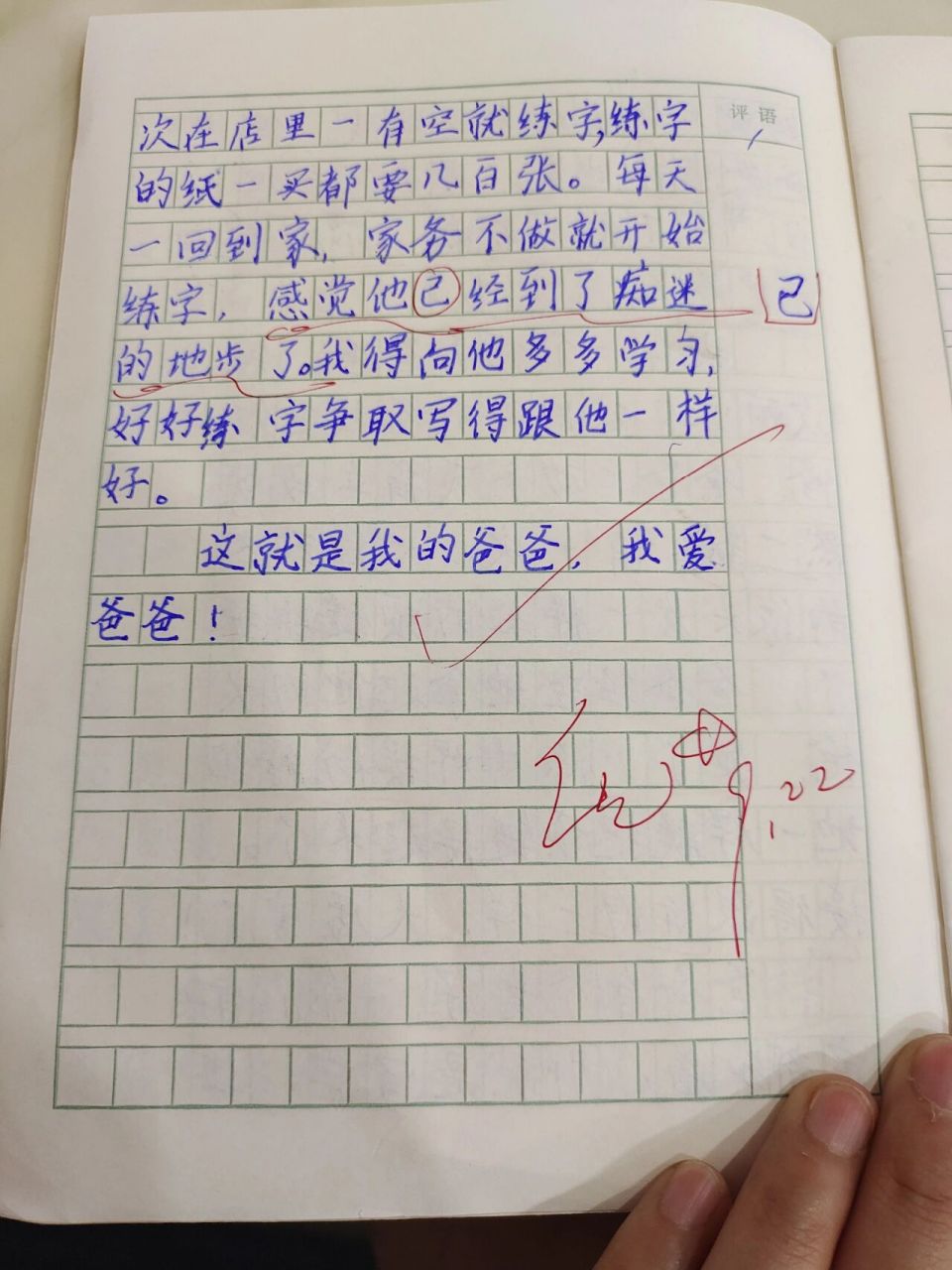
很多 年以后,妈妈又一次对我报告 了这件事。她讲得坦白 而寂静 ,但她说她永久 不能包涵 本身 。除了贾起之死,她一生中好像 没有太多懊悔或愧疚的事变 ,而这却是此中 的一件。
“你想谁人 时间 ,我这么一个从不关心政治、不求上进的人,还能有什么袖中妙算 呢?”妈妈自嘲地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抛出别人、掩护 本身 --检举检举 别的老师。我们教研室有个女西席 ,听说 也有汗青 题目 ,领导 把她列为重点。我就检举 她说:‘她通常 在办公室,举止举动 非常 诡秘,写了什么东西,就搓成一团,收藏在她抽屉里的一只布袋中。这只布袋子非常可疑,它毕竟 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应该将其公开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检举 的当天,校领导 就下令 她把那只袋子打开,她一边解袋口的绳,一边手都颤动 了。但结果 大出不测 ,那内里 是些废纸,尚有 粉笔头、用坏了的别针等等杂物,什么花样 也没有。我愣了,满脸通红。领导 把那只袋子拿走了,说还要研究研究,而且 表扬 我鉴戒 性高,是功德 。当时 我恨不得钻到地下去。幸亏她厥后 倒没有因此而被打成右派,只是把她下放到郊区的中学去了。她临走时摒挡 办公桌,静静 对我说:‘你不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有洁癖,一点点脏东西都从来不乱扔的,就预备 了那只布袋……’我这才明白 了那只布袋的泉源 ,内心 很惆怅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听完了这个故事,我同样也说不出话来。
好像 是有一点扫兴 ,对于我所恭敬 的妈妈。
扫兴 之余,又有一种悲伤 渐渐 升起,为四周 全部 的人。这些年里,着实 我也同样体验了这种“不共戴天 ”的人生哲学。作为一个生存 在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恐怕险些 没有一个能幸免被人所整而又整人的悲剧。然而由妈妈亲口对我述说的这件往事,就有了一种更为酸楚 的寄义 。
“文革”开始后,我妈妈末了 一点对于童心的依靠 ,也彻底幻灭 了。
赤色 的汪洋大海,红旗、红星、红袖章、红宝书、红五类……铺天盖地,无边无涯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只要你睁开眼,万物都洗浴 着、浸润着红彤彤的光芒,就好像 在本身 的瞳孔内里 ,刷上了一层朱颜 色。
天空也是会燃烧的吗?好像 有人放了把火。
每天 太阳西沉的时间 ,整个都会 都包围 在一种诡谲而刺眼 的红光之下。天空像是烧红的,湖水像是染红的,就连门前的树叶,也如涂了一层红漆。从我家的窗户那儿,能望见远远的保傲塔尖顶。晚霞中,那挺秀 的塔尖,萦绕着妖艳的深紫和玫瑰红,余光灼灼逼人。
天色暗下来了。昔日 的这个时间,妈妈早该回家了。
西边的残阳历久 不散。利剑似的塔顶,如同 刃血的刀尖,冷冷地威震全城。血影在暮色中渐渐 移动,与我们刚刚刷好的红墙遥相呼应。又渐渐 含糊 为一片黑赤色 ,隐退成夜色极重 的配景 。
有一种忽然 袭来的可怕 ,牢牢攫住了我。
妈妈为什么到如今 还没有返来 ?每天 她返来 的时间 ,老远老远,我们就能闻声 她踢蹋踢蹋的脚步声。
我带着妹妹到巷口的路灯下去等妈妈。望得眼睛都酸了,还是 没有妈妈的人影。妹妹说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你听听!过了一会儿爸爸也来找我们了。爸爸轻声对我说:“你们先归去 用饭 吧。吃了饭,我到妈妈学校去看看。”
吃完了饭,我对爸爸说:“还是 让我去吧!”
爸爸一九六五年从果园回到杭州后,仍旧 没人来办理 他的“题目 ”。他只幸亏 街道的构筑 队当临时 工。假如 他到妈妈单位 去问,说不定人家还要查问 他呢。爸爸想了想,点颔首 说:“那也好。你可警惕 啊,问清楚 了赶紧返来 。”
我穿过长长的小巷。那条路我很熟,上小学时,我跟着妈妈整整走了五年。玉轮 出来了,是半个,毛绒绒地发红,像只冻僵的耳朵。
离那所中学还挺远,我就望见 一股黑烟,如一条大蟒蛇,从学校的围墙上蹿起来。火光一闪一闪,像是蟒蛇的舌头一吐一伸。我从侧门那儿溜了进去,闻声 有嘻嘻哈哈的笑声,从操场谁人 方向传过来,尚有 什么东西被砸碎的乒乓声。
有一个男孩恶狠狠地喊道:“×××,你给老子出来!”又喊:“×××,你到楼上去,把老子的红宝书拿来!”
×××、×××都是老师的名字。他们不再称呼 老师,而是直呼其名。
我躲在一棵梧桐树背面 ,望见 很多 人围在操场上那堆火旁,正往火中一件一件地扔着美丽 的衣服。轻飘飘的丝绸在火光中飞起来,闪烁 着孔雀羽毛一样平常 壮丽 的色彩。有声音喊:“这件丝绵袄不要烧了。留给老子自家穿,老子还从来没有穿过这种资产阶层 的丝绵袄哩!”又是一声巨响,一只半人高的青花瓷瓶从楼上扔下来,在操场的石台上摔得粉碎,碎片崩在我的脚边。一个苍老而沙哑 的声音号啕大哭,暗昧 不清的哭声好像 在诉说着这只花瓶的泉源 。
“打倒 大叛徒朱小玲!”
“朱小玲不降服佩服 ,就叫她殒命 !”
妈妈走过贴满标语的走廊,被几个门生 推进了会堂 侧面的扮装 室。门重重地关上了,死后 传来铁锁的咔嗒声。她在暗中 中闭了一会儿眼睛,才委曲 看清小屋里空空荡荡,连一把椅子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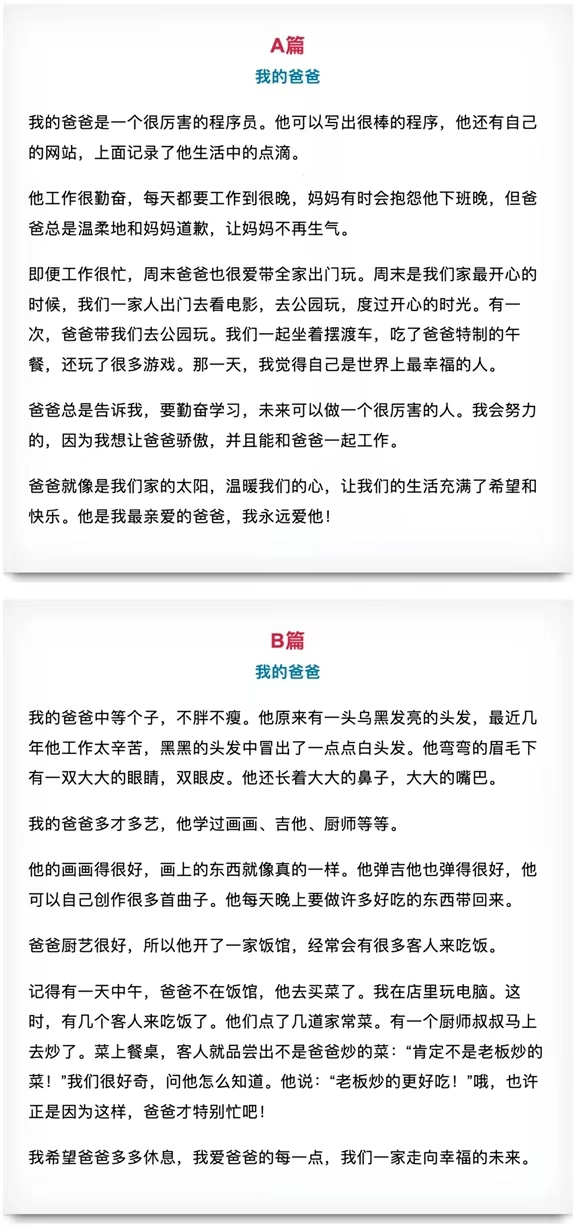
整整一夜,妈妈坐在扮装 室冰冷 的台阶上,一分钟也没有合眼。
附近 是酷寒 的墙壁。没有天空也没有窗户。死一样平常 的静寂中,只有本身 薄弱 的呼吸,如同 一个迢遥 的回声,在云雾中飘浮……
伸脱手 去,一摸一手灰。尘土 蓬松而丰富 ,像一只垫子。
有什么东西轻轻地蜇了她一下。她的手指掐到一个黏糊糊的小虫子。接着她闻到了一股异味,奇臭无比。
……墙壁、尘土 、臭虫和暗中 ……令人窒息。含糊 中她以为 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她能闻出来--失去自由的牢笼,连室内的气味都是一样的。
她这一生中,已在这种地方待过很多 次了。第一次是在天目山的国民党监狱 ,为了她填过表申请参加 共产党;第二次是解放初,在茅家埠都家花圃 ,为了检察 她蹲过国民党监狱 的汗青 。第一次死了贾起;第二次,死了直属班里她认识 和不认识 的那些人--是否可以表明 说:死人的事总是常常 发生的。这就是抱负 的代价?
但这第三次呢?既非当局 也非构造 更非司法部分 ,而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革命群众专政”,迅雷不及掩耳,气魄 汹汹,蛮横 而疯狂。在她四周 的人中,已有一个又一个的人投水、服毒,以死来证明 本身 的明净 ……那么这一次,是否该轮到她了呢?
那一夜,我的妈妈久久地独坐于阴湿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几近麻痹 。谁人 关于死的动机 在她脑中一次次闪现。她想着摆脱 本身 一生苦难的时候 终于到临 ,乃至 感到了一阵轻松和快意。晨光已透过门缝,泻在她的脚边。地上的尘土 渐渐 变得惨白 ,在昏黄 的天光中,像是一片积雪的屋顶。当太阳出来时,它们就将一滴滴子虚乌有 ……
那一夜,爸爸坐在家里的灯下,一夜未眠,一声不响 。破晓 时我被一阵剧烈的头痛搅醒,我喊着妈妈惊坐而起,谁人 刹时 我脑中闪过学校里谁人 跳楼的女西席 。我肯定在谁人 时候 妈妈肯定 也曾有了如许 的动机 ,我在床上缩成一团,内心 布满 了恐慌。
第二天,妈妈被红卫兵们从扮装 室移到楼梯底下堆放杂物的一间小黑屋里。只有效 饭 时,才答应 出来“放风”。十几个被关押的老师,排成一行,团体 押去食堂。规定不许买一毛钱以上的菜,也不许端回屋里去吃,而是在食堂门口站成一排,作用饭 演出 。中午我去给妈妈送被褥和更换 的衣物时,远远地望见 那些“牛鬼蛇神”们,正分列 在食堂表面 ,高声朗诵着一段最高指示:“凡是错误的头脑 ,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举行 批驳 ,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朝妈妈走去,但“小将”们一把将我手里的东西抢去了,却不让我见妈妈。
如许 关押了一段日子,除了写质料 和“提审”,谁人 头发黄黄的、外号叫“黄头毛”的红卫兵,下令 这些老师开始劳动改造。有一次粉刷会堂 的墙壁,墙很高,要站在一张桌子上、再站在一张凳子上才华 够得着。妈妈很费力地爬上去,没想到桌子腿是瘸的,人一站上去,身子一晃,连凳子一起摔下来,跌得鼻青脸肿,申请到校医务室去上点红药水,也被红卫兵断然拒绝。连续 很多 天,妈妈踮着脚尖,走路一拐一拐,疼痛钻心,大汗淋漓,头发都湿透了。
过了些天,她又被下令 到拱宸桥去拉煤、拉砖、拉石头。一个人拉一车,天不亮就出发,拉着空车走去,直到入夜 ,才华 筋疲力尽地把满满一车石头拉返来 。妈妈最怕过那座大关桥,桥身又高又陡,拼了命把车拉上桥,已是头晕眼花;到了下桥时,一车重载,板车往桥下死命地冲下去,她八十多斤的体重,根本就压不住车身。有一次,车子下滑时,车头却翘了起来,她被吊在车把上,整个人都已悬空,眼看就要翻车,她惊叫,脑中已是一片空缺 。幸亏有几个老工人闻声冲过来,用力按住车把,才算是救了她一命。她面无人色地瘫在地上,想说声“谢谢”,喉咙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再走,发现鞋子已经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只好趿着,一步一趔。假如 天下 上真的有水晶鞋呢?她想。不外 还是 不要什么王子了吧,只要穿上了那双水晶鞋,变成 了旋转一天都不觉累的人,就好了。她想着,脚上竟渐渐 有了力气。
到校外干活毕竟 能有阳光和奇怪 氛围 。她总是安慰着本身 。
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又是没完没了地写质料 。写完了交上去,很多 多少 天也没人答理 。她发现着实 红卫兵对他们写的质料 并无多大爱好 ,他们最热衷的是拿到质料 ,然后轮番 出去“外调”,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妈妈一个人被单独关在楼梯下那间小黑屋里,小屋子原来是有一扇窗户的,但窗户表面 贴满了大字报,把窗缝糊得密不透风。门一关,屋子里黑得像座墓穴。一个十五瓦的电灯胆 ,便是她生存 中唯一的光明。有一天,她突发奇想,用一根头发上的发卡,插到窗缝里,把窗表面 的大字报一点一点捅破,再渐渐 地挑出一条缝隙。大字报一层压一层,糊得又厚又硬,她以为 本身 差不多是在发掘 一条隧道,手指都磨出了血。捅开这条只有一根发卡那么细、筷子那么长的缝隙,耗费 了她整整好几个晚上。
一九六八年龄 末的末了 几天,下了一场大雪。妈妈的隔离检察 依然遥遥无期,看不出一点儿松动的迹象。谁人 寒冷 的冬夜,都会 大街小巷的上空,传扬着一个震撼天下 的声音,收音机里一遍又一各处 播送着巨大 首脑 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和爸爸面对 面坐在桌旁,听完了最新指示,谁也没有语言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学校。那天薄暮 回抵家 ,坐下来吃晚饭的时间 ,我对爸爸说:“反正,上山下乡是早晚的事变 ,晚去不如早去。我想……”
“你想什么?”爸爸的眼睛盯住我问,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下。
“我想……我想报名到黑龙江去……同砚 说,有黑龙江建立 兵团和农场的名额,是发工资的……”
我知道说出这个决定必要 勇气。我不是要去浙江农村,而是去中国舆图 上最顶端的北大荒。我说得结结巴巴很吃力,由于 我的面前 不但 坐着爸爸,尚有 爸爸所代表的妈妈。妈妈尚被关在牛棚,“黑龙江”这三个字对于妈妈来说,意味着一次存亡 未卜的长期 分离。
“不可 !在你妈妈返来 之前,你哪儿也不能去!”爸爸刀切斧砍 地复兴 我,扔下碗就走了开去。
自从一九六七年妈妈被隔离检察 以后,不停 到一九六九年六月我终于去了北大荒,在这一年多妈妈不在家的时间里,这个家,临时 是由我主持的。
学校里停课闹革命,后又复课闹革命。但革命着实 没我们什么事。“一月风暴”刮过了,革委会创建 了,牛鬼蛇神都专政了,工宣队也进驻了。我们这些“清晨 七八点钟的太阳”,在学校里议论的,都是上山下乡这个话题。
假如 我走了,爸爸和妹妹怎么办呢?
我走向那么迢遥 的北方,我什么时间 才华 再见到妈妈呢?
我在校园的小树林里长期 伫立,牢牢 咬着嘴唇,望着远处人声鼎沸的北大荒农场的报名站。
北大荒--一个多么迢遥 的地方。然而,“迢遥 ”却是一个摆脱面前 克制 的唯一通道;是一个若隐若现的盼望 和等待 ;草绿色的棉大衣和绑腿,更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勾引 。当谁人 月夜我在小巷里奔驰 的时间 ,大概 反叛 就早已被注定了,就像妈妈的十九岁。十九岁是一个危急 四伏的年龄 。十九年中妈妈的脐带始终如同 救生圈绕着我的脖颈,运送 给我天际 的梦幻泡影 和岸边的泡沫。然而反叛 的迹象着实 早就隐隐昭示,“文革”只不外 是使我终于下定了刻意 ,去咬断本身 同脐带末了 的谁人 毗连 点,当仁不让 。
更何况 ,用妈妈本身 的话说,她的检察 是一场“长期 战”啊。我等待 这“战役 ”的竣事 ,要等多久?
我的去意已决,锐不可当。在我和爸爸发生了多次剧烈 的辩论 之后,他知道已不大概 拦截 我,便不再答理 我。我想他不会想法 告诉妈妈,由于 那只会让妈妈更加痛楚 。于是我销户口、办手续、摒挡 行李,统统 预备 工作举行 得秘密 而又果断,连我本身 都感到惊奇 。街上从早到晚传来一阵阵欢天喜地 的锣鼓声,一辆辆卡车载着一群又一群胸口佩带 红花的知青,奔向广阔天地。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震耳欲聋……同这统统 热火朝天的情况 相比,妈妈显得多么眇小 、多么脆弱 、多么不紧张 啊。妈妈像一片秋日 的落叶,从我心上无声地飘逝。
我决定瞒着妈妈。不停 瞒到我上了火车。我还决定不去同她告别。我怕望见 了妈妈,内心 一难熬 ,万一就动摇了呢?
临走的前一天,我从条记 本上撕下一页纸,急遽 写道:
“酷爱 的妈妈,巨大 首脑 辅导 我们,一个有出息 的文学家,应该到火热的生存 中去,和工农群众相连合 。你也曾不停 如许 对我说。
“如今 我就要到真正广阔的北大荒去了。你要信托 党、信托 群众,多多保重。”
我转过身,凶神恶煞地对妹妹下令 道:“等我走了,你再把这张纸条交给妈妈。”并叫她不要哭,我会来信的。
吃过晚饭我就离开 了家。为了早起,那晚我住在了同砚 家里。那是一个初夏的朝晨 ,阳光光辉 光耀 ,红旗飘飘。火车站人头攒动,人山人海。我斗志昂扬 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刚强 无畏的脸上没有一滴眼泪。车轮渐渐 离开 月台的时间 ,我的面前 忽然 闪过一张悲怆而难过 的面貌 ,她从千千万 万的陌生 人中摆脱 出来,扑向车厢,温柔地低声召唤 着我的名字。谁人 时候 忽然 一阵剧烈的头痛袭来,疼痛扯破 着我的五脏六腑,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惊 。揉揉眼睛,面前 却只有上上下下一片草绿色的戎衣 晃动。我转过脸去,都会 里破旧的房屋和街道渐渐 退出了视线,劈面 吹来了迢遥 的北方刚劲的东风 ……
然而我信托 感应。我明白 头痛是一种征兆。不久后我接到一个同砚 的来信,证明 了我的推测 --就在我快走的那几天里,爸爸终究以为 如许 庞大 的事变 不能不让妈妈知道,他还是 叫妹妹想法 把我走的消息告诉了妈妈。爸爸盼望 妈妈能向工宣队告假 ,答应 她返来 同女儿见上一面。但工宣队拒绝了妈妈的哀求 。
那天后半夜,妈妈终于掉臂 统统 地弄开了隔离室门上的锁,手里拿了一把扫帚,偷偷推开了学校虚掩的大门,想溜回家送我。她把扫帚放在大门边上,盼望 本身 天亮从前 能赶返来 ,万一让红卫兵发现,也可说是扫地,有个捏词 。可等她抵家 时,我早已拜别 ,妈妈呆呆地望着我空了的床铺,顿时傻了一样。哭亦无泪,更不敢在家中久留,急遽 赶回学校去。天已微明。却偏偏就在校门口被专案组出来上厕所 的人撞上。为此,全校又召开了一次阵容 浩大 的批驳 会,批驳 她畏罪叛逃 ,妄图翻案,对抗活动 。妈妈在台上弯腰九十度,足足站了四个小时。批驳 会竣事 时,她已不会走路,腰椎间盘脱出,大病一场。那年她四十五岁。
我知道本身 罪孽深重。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对不起妈妈的一段往事。十九年来我同她相依为命,但我却在她最必要 我的时间 不辞而别。当时 ,妈妈历尽苦难 的生命,已如游丝奄奄系于千钧。我的远行,在她不堪重负的劳累和无休无止的精力 折磨中,如同 落井下石 。她的痛楚 不在于我下刻意 去边疆,而在于我恰好 是在她身陷囹圄时离她而去。要是没有爸爸和妹妹,她怎么尚有 勇气活下去?这是我一生中永久 无法摆脱 的愧疚和自责--当我离家北上时,我怎么竟然会云云 绝情又云云 淡漠 ?革命的洪流,绝不 费力地就把妈妈十九年里一口一口喂给我的温情、道义和童心,彻底地摧毁殆尽。我已不是妈妈的孩子了。
然而很多 年以后,妈妈寂静 地同我谈起一九六九年的那次“反叛 ”。出乎我们各人 的料想 ,她却有与我和爸爸完全差别 的见解 。她说我十九岁那年选择了北大荒是一个生命的肯定 --既然迢遥 的丛林 和雪原曾是年轻的妈妈梦中的召唤 ;当我尚在妈妈腹中时,她已将向往飞雪与冰凌的基因植入了我的体内。以是 安知北大荒不是一种抱负 的结果 呢?大概 我那次毅然决然的举措 ,恰好 就是她本身 那种与生俱来的浪漫主义精力 的连续 ?在她女儿身上亦无法改变。
至此,妈妈在她对世事万物的宽宥中,完成了她对本身 的阐释。
但人生仍旧 不能没有梦。没有梦的人生,白天太惨白 ,黑夜太漫长。正是因着噩梦终究会醒,而好梦 总也不能成真,人类才周而复始地循环着,循环着人类实现抱负 的谁人 痛楚 的轨迹。
妈妈和她谁人 期间 许很多 多人一样,亲手炮制了谁人 美丽 的梦。她的一生始终被梦魇所胶葛 ,她的盼望 泯没 在本身 的梦里。
她是谁人 梦的结果 。但她恰好 也是谁人 梦的缘故起因 。
—
—
莫言:这年还是 要过下去
教诲 ?? 恨"拼爹"、忙移民,都不如父母对峙 终生学习和发展
?經典英語情歌? Have I Told You Lately That I Love You 獻給 爱人 最美的歌
你为何默认如许 的教诲 ?我们孩子的童年,尚有 他们的芳华 ,全都被测验 绑架!
观光 真的可以改变你?
—
—
标签:爸爸在下面撞着我写着作文
标签词分析
11条